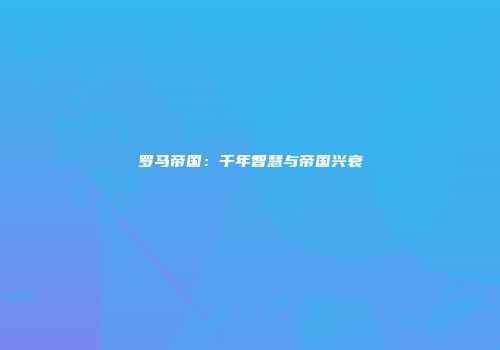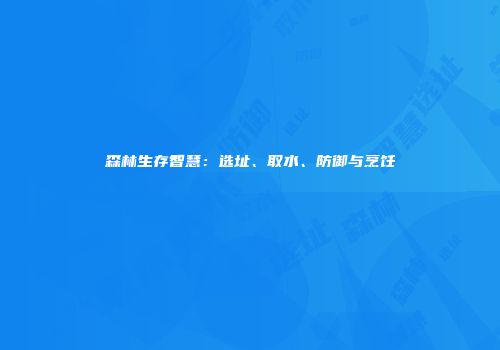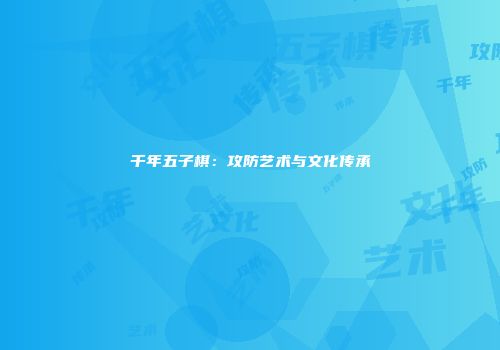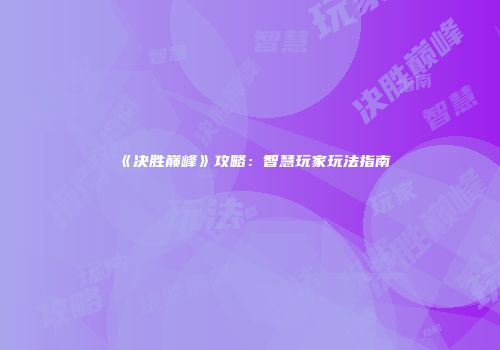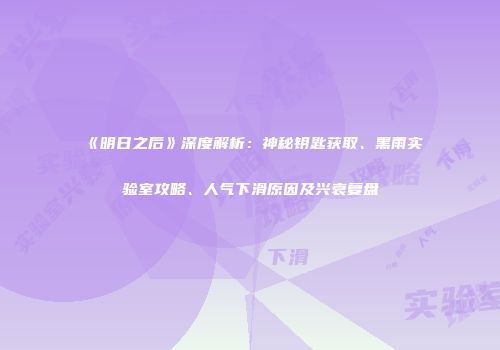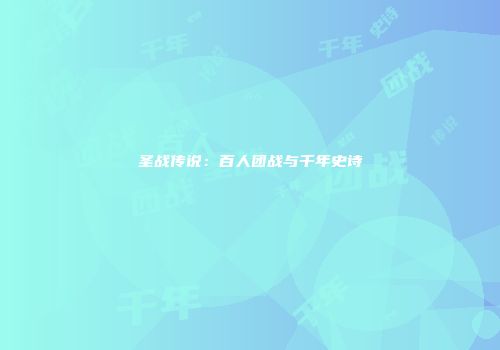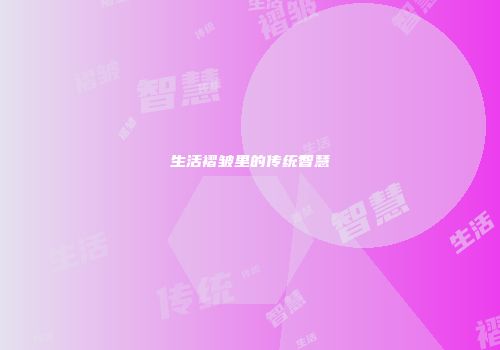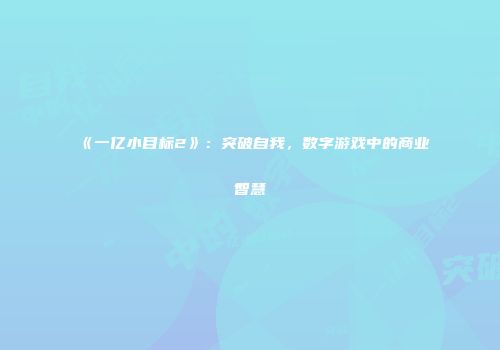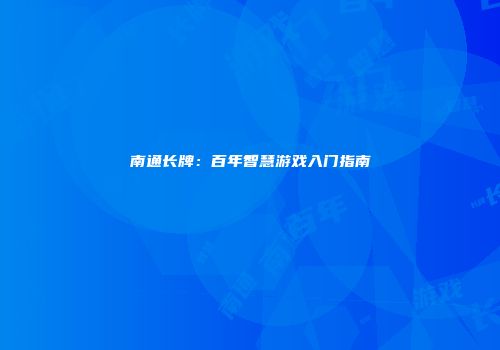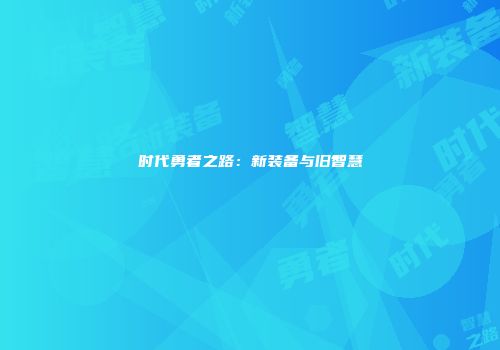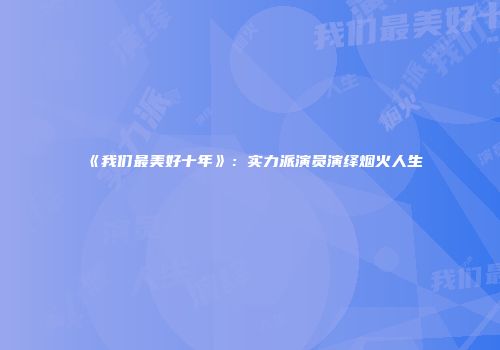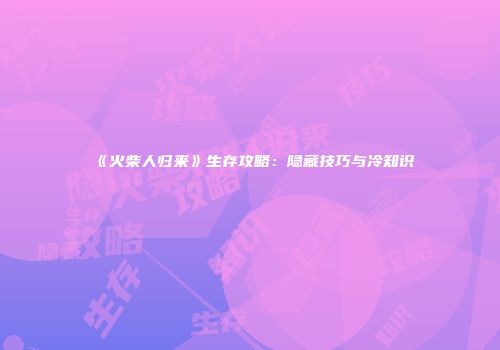罗马帝国:千年智慧与帝国兴衰
站在罗马广场的废墟前,你很难想象这片断壁残垣曾支撑起横跨三大洲的帝国。当导游指着某根残柱说"这是奥古斯都时期的遗迹"时,或许你会突然意识到——这根石柱见证的岁月,比今天纽约自由女神像存在的时光还要漫长五倍。
拼图的第一块:弹性十足的统治框架
罗马人似乎天生懂得"因地制宜"的智慧。公元前3世纪征服意大利半岛时,他们发明了"同盟市"制度。想象下这样的场景:被征服的城邦既不用缴纳贡赋,还能保留地方神灵祭祀,只需要在战争时提供兵源。这种"半自治"模式,就像给不同形状的拼图块都留出了咬合空间。
多元化的权力分配
- 行省总督:手握军政大权却受元老院监督
- 地方议会:保留希腊化城市的自治传统
- 包税人制度:把征税权拍卖给民间商人
这种灵活体系让高卢贵族和埃及祭司都能找到生存空间。对比同时期的秦汉帝国,你会发现长安的官僚体系像精密的齿轮组,而罗马更像可以随时增减模块的乐高积木。
| 治理模式 | 罗马帝国 | 汉帝国 |
| 地方自治权 | 保留地方议会与法律 | 全面推行郡县制 |
| 文化政策 | 主动吸收改造异教 | |
| 军事补给 | 就地征粮与战略粮道结合 | 中央太仓统一调配 |
水泥与剑:硬实力的双重奏
你大概听说过罗马人修路的本事,但可能不知道他们的道路系统藏着更深的秘密。那些用火山灰混凝土铺就的军事大道,每隔15公里就设有换马站,这距离正好是重装步兵半天的行军路程。当信使骑着快马日行300公里时,帕提亚的骆驼商队还在沙漠里数着星星辨方向。
军事机器的进化史
早期的罗马军团像瑞士军刀般多功能:短剑适合近战,标枪用于中距离投射,方阵战术强调纪律。但真正可怕的是他们的"版本更新"能力——面对汉尼拔的骑兵战术,他们发展出更灵活的支队编制;遭遇帕提亚弓箭手,立刻改良盾牌设计。
在《兵法简述》里,韦格蒂乌斯记载的细节让人惊叹:每个百人队携带的辎重中,除了常规武器,还包括木工工具和医疗包。这种"自给自足"的作战单元,让罗马军团像能在任何地形展开的移动城堡。
金币上的统治艺术
在庞贝古城出土的银器店里,考古学家发现了产自西班牙的腌鱼罐和埃及的纸莎草。这种经济活力源自帝国精心设计的货币体系——第纳尔银币的价值三百多年保持稳定,就连边疆的日耳曼部落都愿意接受这种"国际货币"。
不过罗马人最聪明的发明或许是"贬值缓冲机制"。当银矿产量下降时,他们不会直接减少货币成色,而是在金币与银币间建立浮动兑换比例。这种金融把戏,让戴克里先时期的通货膨胀比我们想象中温和得多。
众神的黄昏:信仰体系的崩塌与重构
站在万神殿的穹顶下,你会注意到众神雕像的基座上刻着不同年代的铭文。朱庇特神像可能来自希腊战利品,伊西斯祭坛明显带着埃及风格,密特拉神的崇拜密室则藏在军营地下——这种"神灵大杂烩"本是其文化包容性的体现,直到那个拿撒勒木匠的信徒们出现。
君士坦丁的转变常被看作政治算计,但硬币上的太阳神形象与十字架符号曾长期共存。这种宗教过渡的渐进性,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帝国的生命。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里没说的是,当蛮族洗劫罗马时,他们破坏的更多是行政建筑而非教堂。
瘟疫与气候变化:被忽视的X因素
公元165年从东方归来的军团带回的不仅是战利品,还有天花病毒。安东尼瘟疫夺走了首都三分之一人口,但更致命的是知识阶层的断层——大量希腊语教师病死,导致后来西罗马连能读懂工程手册的人都变得稀缺。
树木年轮研究显示,公元5世纪的地中海气候变得反复无常。北非粮仓的持续干旱与多瑙河流域的异常洪水同时发生,这对依赖粮食调配的帝国来说堪称双重打击。当查士丁尼试图重建帝国时,鼠疫杆菌给了他更沉重的打击。
最后的礼物:法律之城的遗产
特奥多西法典的羊皮卷早已腐朽,但其中"疑罪从无"的原则仍在现代法庭回响。罗马法最精妙之处在于区分"公法"与"私法"——前者规范国家行为,后者调节民事纠纷。这种二元结构像隐形的钢架,支撑着帝国后期的混乱时局。
走在伊斯坦布尔的古老水渠下,摸着那些依然湿润的石块,你会突然明白:真正持久的从不是某个政权,而是解决问题的智慧。当后世君主们争论"皇帝与教皇谁更大"时,他们使用的概念框架,仍是罗马人用千年光阴打磨出来的政治语言。